有一个职业群体,我关注他们很久了,这个群体就是城市垃圾清运工。
关注他们,是缘于我的一个老同学任品德,他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。多年来,在和他的来往中,经常听他讲一些事,讲一些人,并不断地被他们感动着,所以就想亲自体验一下他们的工作。去年腊月二十八晚上,即除夕前夜,终于有机会从头至尾陪他们上了一个班,并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,品尝了他们的百味人生。
晋城方言,垃圾叫圪渣,按时下流行的叫法,就管他们叫“圪渣哥”吧。
鬼不缠
子夜,0时30分,万籁俱寂,寒风刺骨。
明天,不,现在,就进入岁除了。为准备过年而忙碌了一天的人们,大都已进入梦乡。而此时此刻,我却穿着最御寒的行装,站在泽州路小吃城门前,不停地打着哆嗦。
我按约定时间准时到达这里,却不见“圪渣哥”任品德他们。打电话问他怎么回事,才知道因当天的垃圾多,装车比预计时间长了点,不过很快就会路过小吃城。几分钟后,我坐上了任品德开的垃圾清运车。
按垃圾清运公司编组,一辆垃圾清运车配两个人为一组,一个人管开车,另一个人管装卸。他们这一组,由任品德开车,靳文林装卸。任品德是泽州县晋庙铺人,今年51岁;靳文林是泽州县柳树口人,比老任大一岁。
一上车,我就和他们开玩笑说:“你们可真是披星戴月呀!”
老任一句话就把我呛回来了:“你真是个文人,我们每天就是黑来出,白天没。说好听点,就是夜出昼伏,说不好听点,我们就和鬼是一个时点,白天当人,晚上当鬼!”
这话令气氛有点尴尬。我突然想起同学们给老任起的外号——“鬼不缠”,因为每次同学小聚,喝酒划拳,很少有人赢得过他,于是我就说:“你哪里是鬼,明明就是‘鬼不缠’嘛!”
我和老任大笑,不知其然的老靳也跟着笑。
装拉卸
要描写垃圾清运工们的工作场景,才知道真的好难。因为,他们这些“圪渣哥”的工作,实在是太单调乏味了,每天的工作流程就是到垃圾点——拢圪渣——收挡板——吊装——运往垃圾场——卸圪渣——把垃圾罐送回原处。天天如此,循环往复,简单而又平凡,实在没什么精彩之处。但有些小事,却印象颇深。
在连川村的一个垃圾点,路边停放的一辆小轿车,离垃圾罐只有两三米。老任见状,不由得爆粗口:“又是这个狗XX!”老靳说:“要不我去叫主家?”老任说:“算了,我慢慢倒车吧!”进进退退,老任倒了十几分钟,才把车靠近垃圾罐。老任说:“和这家人生气已经不是一两回了。有一次,我们凌晨4点多到这里,但被这辆车堵得怎么也进不去。又是给车主打电话、又是按门铃,可人家愣是两个多小时没反应。天明后,车主媳妇下来,还把我们臭骂了一顿:拉个圪渣,没一点素质,骚扰得我们一晚上睡不好!”由于在此耽搁了时间,他们到第二天上午还没按时拉完垃圾,照例又被领导批评了一通。
在很多垃圾点都能看到,有许多零散垃圾被抛洒在离垃圾罐几米远的地方,老靳他们只好顶着寒风,用手去抠捡。尽管戴着手套,但到后来,他们的指甲、手掌、身上、脸上全是污渍。老任自嘲地说:“咱的工作就是拉—拉—拉!”
我对这些不讲社会公德的人和事很气愤。而这俩“圪渣哥”却说,类似停车堵路、不按规定将垃圾如罐的事太多了,他们早就习以为常了。
恶心鬼
约凌晨两点来钟,我和老靳慢慢地熟络了,一直没怎么吭声的他,也打开了话匣子。
老靳说,咱也不怕你笑话,我们还有一个外号,叫“恶心鬼”。因为我们常年和垃圾打交道,除了脏臭灰,还是脏臭灰。你可能感觉今天很冷,冬天不好过,可对我们来说,冬天比夏天要好过。冬天的垃圾,顶多灰尘多一些,夏天的垃圾,那个脏和臭,你根本想象不到。冬天,我们顶多拿铁锹多铲铲、多拢拢,出点力气、出出汗,也不觉得冷。夏天,隔几天就要穿着水鞋,下到垃圾坑里干活,里面有干饭、稀菜、人屎、狗尿,甚至还有计生用品什么的,混在一起,呛得我们直吐,胃都快要吐出来了。刚开始干这行的时候,我戴了个口罩,但大热天的,本来就满身大汗,戴上口罩,更是难受得要命。时间长了,慢慢对臭味也习惯了。说句玩笑话,现在,我们闻垃圾味,与香油味也没多大差别了。
老靳还幽默地说:“恶心鬼”这个外号,是我们老婆给起的,也只有我们的老婆才能这么叫。要是他人哪怕是孩子这么叫,我们也会跟他闹翻。

任品德(左三)到靳文林(左一)家看望他生病的妻子和老母亲,老靳一家人感到很高兴。
小毛烟
为了拉近距离,也为了御寒,平素很少抽烟的我,专门给他们准备了一包好烟。可我还没来得及拆封,这俩“圪渣哥”就一人掏出一根竹烟袋,还有一个圆圆的铁盒子,里面装着满满的烟丝。他们用拇指和食指捻一点儿,按到烟锅里,大概几秒钟就抽完一锅。
打火机窜出的火苗和烟锅里点燃的烟丝,在驾驶室里时亮时灭。他们一边抽烟,一边交流着毛烟的产地和各自的偏好。老任说,他的毛烟,主要是从老家一个小卖铺买。产自太行山脚下河南省沁阳市山王庄镇的毛烟,抽起来特别带劲,其他的毛烟他一般不抽。老靳说,他的毛烟一般在朝阳市场买,也不知道是哪里产的,他也没有特别的讲究,只要是毛烟就行。他们买的都是1两重的纸包装毛烟,都是3块钱1包,但老任买的没有老靳买的装得满。
我掏出纸烟给他们抽,老靳不好意思接,说他抽不惯。老任说,抽吧,不是外人。我说,抽纸烟不需要频繁地点烟,开着车也安全点。整个晚上,我们三个人没有抽掉半包纸烟,而他俩圆铁盒里的小毛烟却所剩无几了。我说:“你们真抽不惯纸烟?”老靳停了片刻说:“我一个月抽4包毛烟,三四也就十二块钱,就是两盒纸烟的价钱。要抽纸烟,那得多少钱呀?我也想过戒烟,可每天都是整晚上干活,全靠抽烟解乏,没有烟,哪能熬得住呀!”
天天干
现在,我们正常上班的人,每年的节假日、休息日加起来已经超过100天了,可几乎没人知道,环卫工基本上一年365天都在上班,而且是日工资,上一天有一天,一请假,就一分钱也没有了。
老靳说,他到这里上班三年多了,总共就请过5天假。那还是他80岁的老父亲去世后,他晚上要守夜值孝,所以不得不请了5天假。老任在所有的重大节日,压根儿就没请过假。
我问他们,是单位不准假吗?他们说不是。因我知道老任的家庭情况,所以就问老靳:“是你家里没什么家务事需要你请假干吗?”老任当即用他踩刹车的右腿,轻轻地碰我的左腿。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,就不指望老靳回答了。但老靳还是给我讲了他的家事。
苦命人
不知道是不是巧合,这俩“圪渣哥”都是苦命人。
老靳的父亲生前是教师,他给老靳起名文林,其本意就是想让儿子将来能够立于文化之林,吃文化饭。但老靳高中毕业后,却没能实现父亲的愿望,只得与黄土为伴。5年前,老靳的妻子突患肺癌。两年前,他的老母亲又偏瘫了。两个病人,每个月光药费就得三四千块钱,而全年报销的上限才两千块。
我问老靳,那你天天上班,家里的事怎么办?他说,这个工作最适合我干了,天天晚上上班,白天就可以干家务事。秋收夏打时,我白天回村里收割,晚上回来还不误上班;每两个月得跟老婆下郑州看一次病,为了赶时间,早上,我让姑娘把她妈送到车站,我下班后,直接到车站坐车。看完病,当天晚上就赶回来上班,从没间断过。本来,医生说她最多还能活半年,但现在已经5年了,情况还不错。
老靳兄妹共四个,他们体谅老靳,尽量不让他管偏瘫的老母亲,可他于心不忍,还是时不时把母亲接过来尽尽孝。母亲在他家住时,晚上上班前,他要先搀扶老人去租住房外面的厕所解了手,回来给她脱了衣服,安顿她睡了觉才能走。早上下班回到家,第一件事就是给老母亲穿衣服,然后就赶紧给老婆熬药做饭。
我说,你一直这么忙活,能受得了吗?他说,一想到生养自己的母亲和共度苦难的妻子,只要她们安在,我什么苦累都能受得了。再想想他们得吃药看病,我上班也就有了动力。所以,不到万不得已,我就不能停、不敢歇,歇一天70块钱就没了。
38年前,任品德是我们初中尖子班的副班长,是尖子班里的尖子生。无奈,因其父早逝,兄弟姊妹又多,母亲实在无力供他们上学,品学兼优的任品德,不得不辍学,进城当了一名环卫工。30多年来,他也曾开过小车,跑过大车,但阴差阳错,最终还是个“圪渣哥”。十几年前,老任的妻子患了重病,至今一直靠药物维持。6年前,老任的小腿突感麻木,差点瘫痪了。因怕失去这份工作,本来是司机的他,主动申请当装卸工。前年,他腿麻的情况好转后,才又开上了车。
斗死神
若以为这个行业仅仅是苦脏臭灰,那就错了,它其实还面临着危险。垃圾罐的起吊挂钩这个看似简单的操作,需要司机与搭档的高度配合,一旦不慎出现失误,就有可能造成死伤的严重后果。老任就有过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。
那天夜里,也许是天冷,也许是犯困,也许是疏忽,就在他低头安装垃圾罐挡板时,司机就将挂钩放了下来,重重地砸在他的头上。顿时,他只觉得天旋地转,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闻讯而来的工友们见他头上流血,就要送他去医院,可他醒过来后,却坚决拒绝去医院,而是执意回家。他自己在家擦了点白酒,盖了块纱布,戴了顶帽子,第二天晚上继续上班。过了几天,伤口实在疼得不行,他才去一个小诊所看,医生简单给他处理了一下,建议他去住院,他却硬撑着,最终也没去。
我说,你应该给领导申请休工伤假,或许还能当劳模呢!他说,这又不怨领导,报上去不是给领导出难题吗?他还给我讲了一件更让人后怕的事。
有个新司机,到中转场倒垃圾时,由于技术不熟练,一下子把净重一吨半的垃圾罐,掉到十几米深的密封罐里了。没办法,他又自作主张,把绳子绑在腰间,下到密封罐里往上吊垃圾罐。不料,吊到半空中时,绳子断了,把他摔了个粉碎性骨折。幸运的是,垃圾罐吊上去了,不然的话,连罐带人掉下来,他绝对性命难保。而他住院后,给单位提的唯一要求就是出院后让他继续上班。
苦中乐
这些故事,听起来很沉重,但他俩讲的时候,却轻描淡写,好像与他们不相干似的,没有一丝抱怨。相反,他们对生活特有的满足感,却充满了正能量。
我和他们讨论对幸福的理解,他们的回答让我感到意外。
老任说,和老靳一比,我就幸福了。不管严寒酷暑,每到一个垃圾点,我坐在遮风挡雨的驾驶室里,动动手脚就行了,老靳还得到垃圾堆前具体干活。有时候我不高兴了,还拿老靳当出气筒。
老靳则说,和老任一比,我就幸福多了。车一开,一路上我随时可以打瞌睡迷糊一会儿,老任却一点儿也不敢松懈。
老任说,我家只有一个病人,而老靳家却有两个病人,我比老靳幸福。
老靳说,我好歹有个老娘,而老任却几十年都没叫过娘了,还是我比老任幸福。
他们就是用这种近乎调侃的方式,来相互感恩、相互激励、相互幸福着。
我又问他们对自己职业的看法。他们说,三百六十行,哪个行业不得有人干?老任反问我:你说我们“圪渣哥”和省长比,哪个岗位好?我笑了笑,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老任说,我自己觉得,我们“圪渣哥”这个职业竞争不激烈,没有人和“圪渣哥”争抢,只要有口气,就能一直干,今天“圪渣哥”,明天“圪渣哥”,后天还是“圪渣哥”……
整个夜晚,垃圾车在市区大街小巷与垃圾中转场之间来回穿梭,不知不觉中,垃圾就没了,黑夜也走了。腊月二十九早上7点,我和“圪渣哥”分手,老靳要回柳树口老家贴对联,老任要去政府春节蔬菜粮油副食品供应点排队置办年货,而我则想赶紧回家冲个澡,美美地补上一觉。
可回到家后,我却怎么也睡不着。一想到今天晚上我将坐在电视机前,陪家人看着春晚,嗑着瓜子,制造着垃圾,而“圪渣哥”们却还得重复昨晚的故事,心里就觉得不忍。昨夜的场景不断地在我脑海里回放,“圪渣哥”的形象不停地在我眼前放大,一股激情催促我打开电脑,要把他们的故事讲给大家。
这俩“圪渣哥”,仅仅是咱们市区近千名环卫工人的一个缩影。他们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用个人的脏苦,换来了城市的美丽。这样的人,不就是我们每个市民最最应该感恩的人吗?不就是我们要寻找的晋城好人吗?
希望每个市民倒垃圾时,多走一小步,把垃圾倒进垃圾罐里,以减少他们工作中的麻烦。更希望有车的市民,不要将车停靠在垃圾站点的通道里,以免他们不得不“从晚上一直等你到天亮”,白白地耽误他们几个小时。
如果每个市民都能够独善其身,做好那么“一点点”,就是对环卫工人最大的支持和感恩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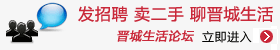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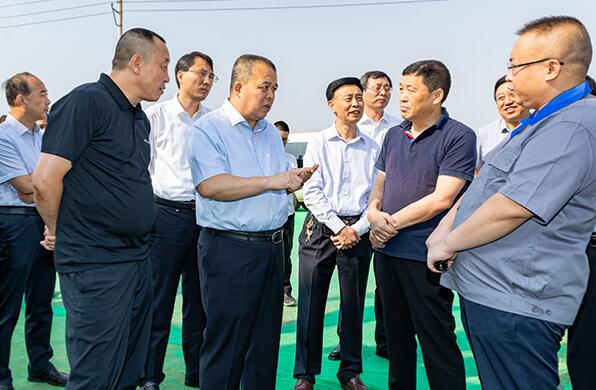








 晋公网安备 14050002000555号
晋公网安备 14050002000555号